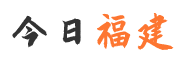●高峰
●高峰 临近五月,雨水渐渐稠了。路上常汪着水,倒映着灰蒙蒙的天。这时候,乌梅就该熟了。 乌梅树在我们那小城里不算稀罕物。寻常巷陌里,偶有一两株从人家院墙内探出头来,枝干黝黑曲折,颇有些古意。树不高,却生得极有筋骨,摸上去粗粝得很。叶子卵圆形,边缘有细锯齿,叶面泛着蜡质的光。花开得早,三月便见白花簇簇,不甚起眼,却自有一股清冽香气。 我家后园原有一株老乌梅,是父亲年轻时手植的。乌梅初结时青碧如玉,硬邦邦地挂在枝头。待到五月,日头渐渐毒了,那果子便由青转黄,由黄而红,最后竟成了紫黑色。这时节的乌梅最是好看,黑里透红,红中泛紫,表皮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。 摘乌梅要趁清晨,露水未干时,果子最是饱满。记得儿时随父亲摘梅,他总教我挑那些黑得发亮的,说这模样的最甜。我性子急,常等不得它熟透,摘了半红的就往嘴里送,酸得龇牙咧嘴。父亲便笑,说人生三味,酸为其一,早尝早好。如今想来,这话里竟藏着几分禅机。 乌梅的滋味,实在难以言表。初入口时酸得人打战,但那酸中又带着丝丝缕缕的甜,像是故意与人捉迷藏似的。含久了,酸味渐褪,竟泛出些蜜样的回甘来。最妙的是那果肉,熟透的乌梅肉极软,几乎不用嚼,只在舌尖轻轻一压,便化作一汪酸甜的浆汁,顺着喉咙滑下去,五脏六腑都为之一振。 熟透的乌梅不过拇指大小,形如缩微的李子,顶端有个小小的凹陷。果皮极薄,轻轻一掐便破,流出紫红色的汁液来,染得满手都是。这汁液很顽固,沾在手上要两三日方能褪尽。小时候我们常以此作墨,在纸上涂鸦,倒也自得其乐。 我们那地方吃乌梅的法子多。最简单的是鲜食,洗净了直接入口,最能得其本味。讲究些的妇人会将乌梅与冰糖同煮,熬成乌梅汤,夏日冰镇了喝,最是解暑。也有用白酒浸泡的,月余后启封,酒色绛红,酸甜适口。至于乌梅干、乌梅酱之类,更是家家必备的零嘴。 我尤爱母亲做的乌梅糕。取熟透的乌梅去核捣烂,和以糯米粉,中间夹一层红豆沙,上笼蒸熟。出锅时乌梅的紫红渗入雪白的米粉中,呈现出一种朦胧的淡紫色,煞是好看。这糕点酸甜软糯,吃多了也不腻,配一盏清茶,便可消磨半日时光。 乌梅核也不浪费。洗净晒干后,可作“弹子”玩。我们小时候常在巷子里比赛,看谁的乌梅核滚得远。那核呈扁圆形,表面布满细密的纹路,黑亮如漆,是天然的玩物。有时运气好,还能捡到形状特别周正的,如获至宝。 岁月流转,乌梅依旧在每年五月如期而至,酸酸甜甜的滋味,不仅留在舌尖,更承载着过往温馨的回忆。 (来源:集美报)
文章链接:http://www.dongfengkuaidi.vip/news/show-119017.html
更多>同类资讯
0 条相关评论